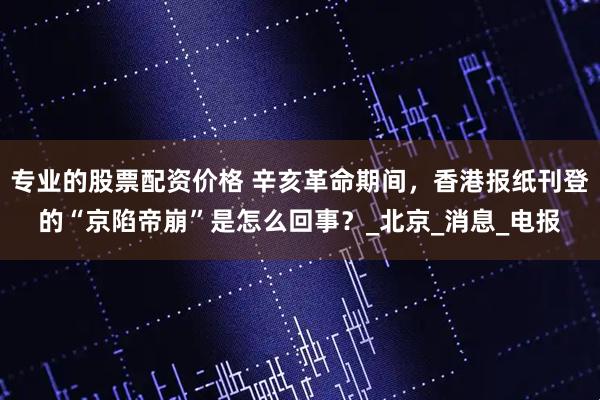
中国进入传媒时代,已是20世纪初,清廷实行新政。逐渐开放报禁,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,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,也敢放言无忌。即便是革命党人,只要有银子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,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杂志,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,也可办报暗中宣传革命。如果被发现了,大不了关门了事,改换名称再办一家就是。
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,原本就人心浮动,陆军大臣荫昌出征讨伐,盛宣怀送行,嘱托他千万保护好汉阳钢铁厂,保护好了有重赏。荫昌爽快地回答说,你准备好钱就是了。结果被记者听去,解释成朝廷军饷不继,结果导致银行发生挤兑。有意无意之间助了武昌革命军一臂之力。
当时多数的报纸都倾向于革命,所以,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,往往对革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如果革命党方面胜利,就夸大战果,失利则巧加掩饰。对于各地的响应与骚动,也大多加以渲染。弄得满城风雨,举国狼烟,使得整个清廷,风声鹤唳,人心惶惶。达官贵人,纷纷跑往天津租界。当时的朝廷当政者,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,缺乏政治经验,更没有应付传媒的手段,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真伪。所以,在媒体有意和无意的“新闻战”面前,显得惊慌失措,进退失据。
展开剩余70%当时的“新闻战”,有一部分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。一个很有效的战术,就是夸大其词。把蚂蚁说成大象,把芝麻说成西瓜。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,令人难以辨别。当然,也有急性子的,干脆直接编造,凭空弄一个假消息来,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。
当时的通讯,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。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,架设了电报线,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。官方的电报局,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,但空闲的时候,也允许拍发些民用电报。
清朝末年,上海已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,报业最为发达,北京是政治中心,所以西洋的外文报纸往往把总部设在上海,在北京派驻记者,把每日的最新消息,用电报传到上海。后来,上海几家大的中文报纸,也纷纷效法,在北京设通讯员,每日打探消息,然后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。至于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缺乏经费的“穷报”,也有自己的办法,那就是闭门造车。据说,凭着政治嗅觉,有时还真编得煞有介事。
当时的香港,比起上海来,还是个小地方,至多算二流城市。传媒不甚发达,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,是《循环日报》。它报道大陆的消息,也得靠专电。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,所以,《循环日报》就在上海派驻了一个通讯员,专门给拍发有关内地的新闻,至于北京的消息,就只能通过别的报纸间接获知了。
当辛亥革命爆发,各地骚动之时,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,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,于是结识了《循环日报》驻上海的通讯员。当时广东尚未独立,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,还在顽抗,只同意保安(保境安民),不希望独立,革命党一时半会儿也无办法。那位华侨觉得,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,造点事端,给广东官方制造点混乱与压力。于是《循环日报》驻上海通讯员就拟了一条“北京专电”:“京陷帝奔”。这位华侨觉得还不过瘾,改为“京陷帝崩”。通讯员犹豫了一下,就这样发到了香港。这个所谓的“新闻”实在是太惊天动地了,香港《循环日报》接电后,一时也拿不准,没敢发表,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。通讯员有些慌,忙问华侨怎么办?华侨说,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,无法核实。连电报都不通了,京城可是真的陷落了。于是香港方面就信了,一时间,登载大字“京陷帝崩”消息的报纸,传遍了整个香港。据当时民众回忆,全港华人,闻此消息欢声雷动,举市若狂,纷纷燃放鞭炮,上街庆祝,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,英国警察都无法止住。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比较自由,并没有太多障碍,不需要通行证之类。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,马上就传到了广州。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,跟北京有电报联系,自然不太相信,但底下的人,道听途说,香港那边报纸已经登了,京陷帝崩,北京完了,皇帝翘了,那个不慌呢?总督、提督以下的人员,个个惊魂不定。总督就是出来辟谣,也未必有人信。显然这个假新闻,对广东的局势影响颇大。直至全国光复后,香港报纸才知道他们当初报道的其实是个假消息。但是,这个谣言“政治正确”,所以,之后也就无人追究。
到了民国之后,新闻媒体更为成熟了,偏向难免。但公然造谣,是不大敢做了。毕竟狼来了,喊一次两次行,喊多了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,报纸就没人问津了。
发布于:湖南省宜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